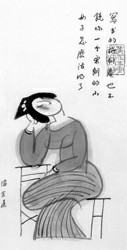


《水滸》之潘金蓮 黃永玉
與鮑鵬山認識已十多年,距讀他的《寂寞圣哲》到今天也有九年。其間各有事累,難得存問。但有一個情景一直記得。那是在一次國際會議上,坐在底下的他,對滿臺的高頭講章實在不耐,舉手發(fā)問:你們?nèi)绱嗣撾x開文本談問題,有意思嗎?
這里要說的不是鵬山的率直,做學問的人未必有此就是大德,而是他對這樣一種治學方法的執(zhí)著肯認與實踐。當上世紀八十年代,人們爭先恐后地引西學來裁量傳統(tǒng),不僅視角與方法,即標題和出注方式也一味擬同西方,而全不想彼之所以如此,有從語言到文化各種先天局限的影響。譬如,因為無法圍繞多個對象窮盡搜討,海量釋讀原典,只得選一人一事作精細的討論;又因為難以覷定一個問題作擘肌分理的博觀圓照,只得在注釋中另為申論,以求合照。對這種但取小徑,勿由大道;或橫生枝節(jié),強為安頓,乃至以跟風為“預(yù)流”,牛花繭絲,都拉開架勢辨析,屑小物事,充全副精力發(fā)揚,鵬山最不樂見。盡管,這樣的情形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(jīng)消停,在有的領(lǐng)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。但他能不為搖動,執(zhí)拗地做自己喜歡的學問,既努力貼合文本,深入體味,又力避哲學的矯情與思想的做作,越十年不改而至于今,真的使自己的論說,揭開了文字背后的曲曲窔奧,還原了人性的深層結(jié)構(gòu)。
他的《新讀諸子百家》著意探究先秦諸子的思想及其后世影響,尤著力描述在古代中國特殊的地域、文化背景下,人的坎坷命運與心路歷程。其間,個人與體制調(diào)適過程中產(chǎn)生的種種情偽與變態(tài),最引動他的關(guān)切,是以筆墨所及,每有新見。如稱莊子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對普通人說話的人,“莊子之住鄉(xiāng)下,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選擇”,意在發(fā)見莊子思想對當日社會種種荒唐罪惡的拯救價值。又稱屈原之影響中國歷史不在其思想與事功,而在其失敗,那種“個人對歷史的失敗,個性對社會的失敗,理想對現(xiàn)實的失敗”,將一個政治上不成熟的敏感詩人之于過于圓滑的涼薄世情的緊張關(guān)系,揭示得入木三分。
他的《中國人的心靈》還原的是中國文學的整體發(fā)展歷史,就其當初的本意,是想寫成文學史的,但最后的面目與一般文學史的呆定老套全不相干。相反,基于“文學是人類精神的避難所,并且將被證明是最后一個”的認知,它更多地將視角對準人心與人性,尤注意選取歷代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或觀點主張,有時一花一吟,幾個字的賞析,照見的是三千年來,中國人理智與情感的關(guān)竅和肯綮。至于所揭出的“傷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”,不但有人類基本的心理事實做依據(jù),更符合古代中國人對人情事理的深徹體知。或以為,傳統(tǒng)的中國,自有一種“樂感文化”,如王國維所說,“吾國人之精神,世間的也,樂天的也,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,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”,但他看來,不管從哪個意義上論此“樂”字,“中國人骨子里就是悲劇性的”,“在中國人的感受里,一切美好的東西幾乎都是令人傷感的,因為我們窺見了繁華背后的憔悴”,從這個意義上,毋寧說它是“哀感”的更通。“只是,一個出人意料的結(jié)果是,由于我們能充分體認到世界的荒謬與人生的悲涼,我們在日常表現(xiàn)上,往往倒是樂觀的”。但凡讀過莊子、陶淵明和蘇東坡,我們就會承認,作者的判斷很有道理。
這里說到戲曲小說,它們也是本書的一大重點。作者對此,特別是對文學史上那幾部代表性的經(jīng)典小說,有十分精到的討論。如認為對《紅樓夢》中的人物不易硬做好人壞人的判分,像有些無聊的紅學家的那樣。賈政、鳳姐和襲人等在“道德上固然不高尚,但他們的缺點,卻也是在基本的人性范圍之內(nèi)”,正因為如此,這種普通人性造成的情感悲劇,才讓人真正的感慨萬端。又指出《三國演義》的道德水準與趣味都是民間的,既顯得保守,又極為庸常;語言雖稱精致,文學成就卻甚為可疑。比之《西游記》來,語言雖顯粗俗,但因取一種破壞與看穿的立場,反而更見識見的高邁,并更合符士人的趣味。而就它的主題而言,既無關(guān)壓迫與反抗,也不為爭底層的自由,只是有旺盛的生命力需要發(fā)泄,所以,小說中對立的雙方不過是游戲的雙方,又因作者對這雙方力量對比的預(yù)設(shè)明顯,遂使“閱讀的快感就不來自什么懸念與結(jié)局,而是轉(zhuǎn)向了對過程本身的欣賞”。小說中對具體人物如果說仍有褒貶,也多由社會層次轉(zhuǎn)向人性的層次,由反映社會矛盾轉(zhuǎn)向人性的缺陷。
此外,他還指出《儒林外史》主題之深刻在于“反體制”,在于對這種體制外無所謂成功光榮、體面尊嚴的單一價值觀,及其對人性的擠迫與扭曲有深刻無比的鞭笞。當然,儒林外更廣大的市井也是如此,他照例通過比較來說道理。他告訴人,在《金瓶梅》中,究竟商人的金錢侵蝕了權(quán)力,還是權(quán)力導致了商人的墮落,是一個需要思量的問題。當國家公權(quán)力過度占有社會資源,一切不道德才更容易產(chǎn)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類似西門慶這樣的,就可視為權(quán)力的受害者。小說中的他,在社會通行的語境里,不過是一“無惡不作”的壞人,但看看吳敬梓筆下的嚴貢生,一個被體制認可的“優(yōu)行”的鄉(xiāng)紳,實際上卻“無作不惡”。兩者相較,后者是不是更寫出了一種壞的體制和價值。于此,作者的結(jié)論是,“好的價值會判斷壞人,而壞的價值則不能”。
凡此種種,入情入理的評判,不惟畫人眼前,還畫人心上與意外的洞徹與精到,更豐富地呈現(xiàn)在他對《水滸》的解讀上。在他看來,作者之所以寫此,無關(guān)農(nóng)民起義,只是為了釋放一肚皮的錦繡與牢騷,寄托對寒涼人世中一種溫藹暖意的思慕而已。其實,關(guān)于《水滸》是作者一瀉胸中之積郁的產(chǎn)物,從金圣嘆到胡適之都這么說,但可能他們說得簡切了,今人偏不能信,也無從信起。鵬山以精細的分析,精辟的提點,抉幽顯微,發(fā)覆祛魅,當他說“酒是我們和這世界妥協(xié)的理由和條件,酒調(diào)動的是我們自身的體溫,卻讓我們感謝世界的溫暖”,風雪山神廟中,林教頭的英雄末路,是不是給你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!他還說,《水滸傳》的妙處,金圣嘆還沒有說完。這是一個重要的結(jié)論,對照我們一上來說的他的率直,真是有意思得緊。只是,我也曾在電視上看他說林沖,或許為了照顧大眾的接受,多只是“非常非常”、“很好很好”之類,這還是鮑鵬山嗎?
遺憾的是,現(xiàn)如今人們只認識這樣的鮑鵬山,并只知道開電視機有趣,相信開卷有益的日少。孰不知圖像與聲音更多刺激感官,不砥礪思想,它更容易造成的是被動的接受與膚淺的觀察。哪里像閱讀,能調(diào)動人整個心靈,形成思維的緊張。并且只有在閱讀中,人才能體會一部好的作品,實際上就是一個開放的召喚結(jié)構(gòu)。以是否抵達這個結(jié)構(gòu)作標準,在電視上,鵬山只做了吆喝的買賣;在他的書里,包括已出的《新說水滸》與《新說水滸2》,我們才見到一個熱忱而有見識的引路人,他以與古人“結(jié)心”之所得,告訴你必須知道并且也應(yīng)該可以理解的更深刻的東西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他無疑是一個寫得比說得好的人。

